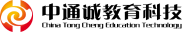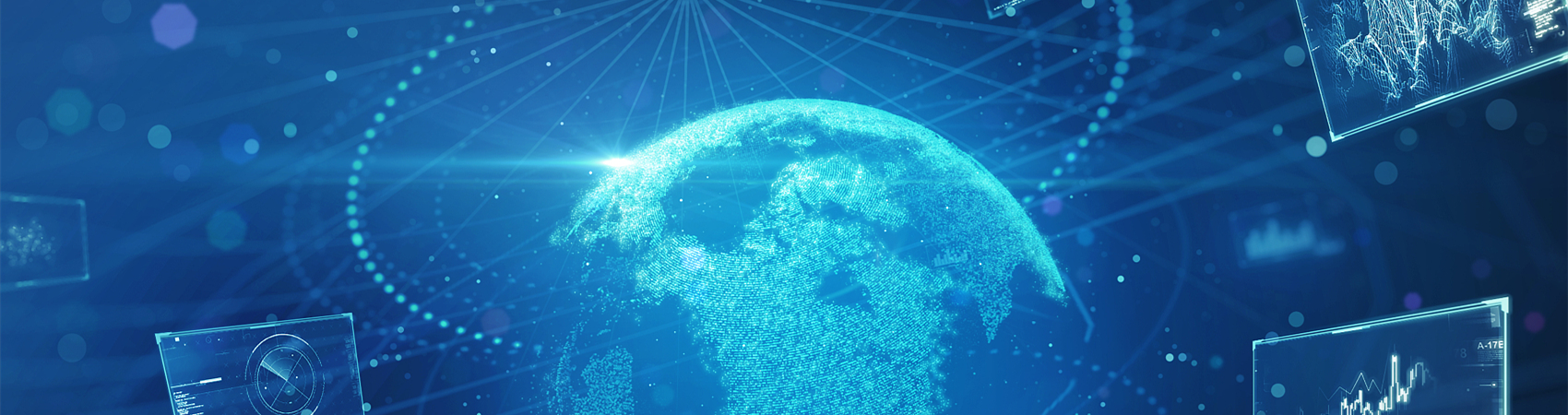最严大基建新规来了!中央明确,违规者将全部叫停
大基建时代,从9月1日起,将彻底转向。
近日,财政部、住建部等六大部门联合印发了最新政策文件《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(试行)》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,明确了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的管理规范,支持和推动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,该文件自2024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。
其中,第十三条明确规定:严禁为没有收益或收益不足的市政基础设施资产违法违规举债,不得增加隐性债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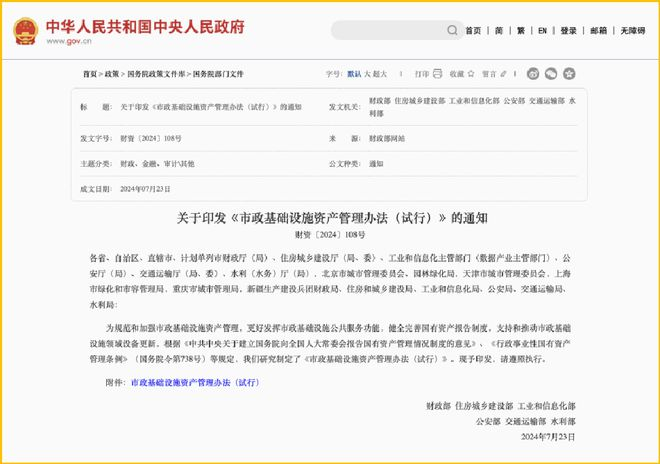
这里的市政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地铁、有轨电车这类大型交通,更进一步细分为城市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公交场站、广场、公园绿地、环卫、排水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热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设施等等。
这意味着:当然,并不是说这些市政项目就彻底不能搞了,如果你用盈余财政资金来搞,那没得说。但,你要是想借钱来搞?那不好意思,项目必须有收益率才行,如果收益率覆盖不了债务本息的,那就不准搞,更不准偷偷摸摸地借钱来搞。简析:据波哥看楼市观察,这个政策主要是在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的角度,进行了系统和严格的设计,其最大的亮点是“是否有收益”、而且必须是足够的收益,这一点作为此类基建项目的核心评判标准,否则就不能上马和实行严格的问责等。
也即,充分从严格的财务范畴,来审视每一个大基建项目在投资和收益上的具体指标,不达标者必须下马。也就是说,原来很多地方和很多人那种“投了再说,赚不赚钱是后面的事情”的想法和模式,就再也站不住脚了,因为收益是要看到真金白银的,做不了假。此外,上述第十三条里面,还带了一个尾巴——“不得增加隐性债务”,这相当于是第二个严格约束,估计很多人没怎么注意或没太看明白,可能将其跟违法违规举债混为一谈了。
这是什么意思?在波哥看来,其实这是一个堵漏洞的设计,因为根据“收益必须达标”的原则,在实操中,还会出现一个“投机”的情况,很多地方以前都用过的一招——就是“巧妙”转移债务或投资成本等,这样就能自圆其说和瞒天过海。例如,近期公开的北京市2023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称,昌平区47.90亿元转增区属国有企业权益,债券项目收入归属企业,还本付息责任由区级财政承担。因此,想化整为零和转移出去,这条路也走不通了,而把地方政府大基建投资的目光,全部引导和聚拢到收益必须达标这一点上来,而不要再去搞那些花花肠子了。也即,该政策在“显债+隐债”两个方面做了严苛的约束,只想借债投资或扩张,不考虑实际收益,都是“耍流氓”类的大基建投资行为,必须快速叫停。比如,过去10多年来,一些地方大规模扩张地方专项债、城投债,只重GDP增长,不重债务风险管理,只建不管,不清楚资产家底,职责不明,管理能力和水平也跟不上,甚至在债券资金管理上还出现了“债券项目收入归属企业,还本付息责任由财政承担”的不规范现象。
毕竟,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再也经不起瞎折腾了。那么,又有哪些比较经典又奇葩的案例呢?下面,简单介绍几个,以供大家参考。
比如,非常“有名”的贵州独山,在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的情况下,却大肆举债400亿去打造“天下第一水司楼”,用了该区域年度收入的40倍杠杆去举债,可见有多么的疯狂。
比如,靠烂尾这一行为艺术而出圈的贵州六盘水,据报道,在2013年到2017年李某勇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期间,一口气推动了23个旅游项目的建设,其中有16个项目列为“低效闲置项目”,基本就是“烂尾”了。在李某勇主政的三年里,当地新增债务高达1500亿元,而全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不到100个亿,其杠杠也高的吓人。
比如,海南在环岛高铁上,投资4000多万元投资建的儋州海头站,自2015年西环高铁开通以来都没有正式启用过——因为每天的乘客只有几十号人,收益根本覆盖不了成本,只要启用就是亏钱,一年白白地要亏五百万,还不如不启用。2023年底,海头站终于开始启用了,但在东环高铁线上2010年就修好的万宁和乐站仍未开通.
比如,今年年初,甘肃天水因举债上马建设有轨电车项目而被通报。一期线路年收入仅160万元,而运营成本约4000万元,二期工程因资金投入不到位迟迟未能建成。
比如,在湖南湘潭,该市原市委书记任上大肆违规融资举债,导致湘潭市新增债务435亿元,33个工程烂尾。
此外,一些地方高铁建成之后,也出现了闲置多年的窘况。
据媒体报道和统计,全国至少有26个高铁站建成后,因位置偏远、周边配套不足、客流量低等缘故,处于未启用或关停状态。